文物鉴定家史树青访谈
解说:坐落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全国最大的历史文物博物馆,这里也是史树青先生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至今,馆里有重要的鉴定活动还是会请已经退休的史老出马。1946年,从辅仁大学完成学业的史树青来到了当时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国立历史博物馆,从此开始了他的职业鉴定生涯。仅仅几年后,一件后来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珍品——元代成吉思汗画像,就经史树青之手走进了博物馆。
史树青:1952年的时候,刚解放啊,我一个小学同学叫崔月荣,女的,她丈夫让我看东西去,他说“我这个烂书要卖,烂画要卖。”我就看了。就选了这么一张画——书都是一般的书——这个画我说我们要。三两块钱,三五块钱。
主持人:也是很便宜。
史树青:都是很便宜,
解说:这幅成吉思汗的画像就是史树青当年花几块钱买回来的,成吉思汗画像过去仅见一幅,为明朝人仿制的。而史树青发现这幅画中人物的服饰与《元史·舆服志》中的记载相吻合,很有可能是元朝的画作。如果是成吉思汗生前所画则将更具历史价值。
史树青:我认为这是旧画,我也没敢说这是元朝的东西,或者是蒙古时期的东西,后来张珩、谢稚柳、启功先生他们鉴定这是元朝画,很有意思。
主持人:那您后来有没有考证过是成吉思汗在世的时候画的吗?
史树青:是成吉思汗死后画的。这些画像基本都是影像,都放在影堂里头,上供用的——过年过节上供,祖先堂
主持人:那应该是成吉思汗去世之后,画工凭着记忆画的。
史树青:画工根据他的记忆,或者根据他的遗体的样子,或者根据他子女的样子,
主持人:从这里来断定的话,他应该跟成吉思汗真实的容貌很接近了。
史树青:很接近了。这个画像很有意思,这个风俗啊——到后来也是这样子——这个人死了画像,往往这个给死人画像都得什么呢,死人躺在那儿你在死人对脸画,给他画像。骑在死人身上。
主持人:过去是这样画吗?
史树青:是这样画。
解说:这幅画像突破了博物馆关于成吉思汗文物零的纪录,因为当时还没有一件成吉思汗的文物实品。这块珍贵的成吉思汗腰牌也是后来史树青为馆里征集的,但与成吉思汗的传世画像相比,这块腰牌的故事却要曲折得多。因为它,史树青还得罪了不少人。
史树青:有一天有一个人拿着这个腰牌到我们博物馆来,来鉴定来卖,结果我们接待的人就说这个是假的。
主持人:这是哪年啊?
史树青:这是前七八年吧。
主持人:那时候假的文物已经有不少了。
史树青:有不少。他们说“这都是假的,不值钱,我们不要”,正好我从门外进来,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呢,他说这是一个腰牌,给你们你们不要,我一看这是真的,我说你先别走,我请你吃饭。中午,问他多少钱买的。他说我是八千块钱买的,你们给我点儿赚,给我九千块钱我就卖给您了。我说这个东西您先吃完饭再说。到下午了,我就跟他们研究,就请馆长来了,第一把手,馆长一看假的不要。他是领导啊。我就给卖这个的人记下来地址什么地方,说大成县什么什么地方。我说这是好东西。我说这个馆长不要的话——我赌气的话——我自己要都可以,我将来捐。
主持人:我还想问您这个问题呢,您可以自己要?
史树青:不可以自己要。这是公家的事,这么好的东西能自己要吗?
主持人:博物馆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规定:您不能够自己去收藏?
史树青:就怕这个,就怕给公家送来了,您看着好,自己收了,这是道德的东西,职业道德的东西,犯罪的。
主持人:这种事您是肯定不会做的。但是这个腰牌当时博物馆是明确不要了。您当时为什么没有想到自己要这个腰牌呢?
史树青:这个东西是给博物馆,我们追求博物馆的文物,追求了50年了,我们陈列室陈列成吉思汗,这位政治家的文物,我们就一件文物也没有,就有一件画像。
主持人:所以您最大的愿望是把它征集过来。
史树青:征集过来是陈列的需要啊。就有一个成吉思汗的画像,底下什么成吉思汗的用具、纪念品什么都没有,这儿来一个硬货,来一个纪念品这还了得。我们征集成吉思汗的文物哪儿征集去,没有啊。
解说:“成吉思皇帝圣旨金牌”,银质鎏金,长21.7厘米,宽6厘米,是蒙古国皇帝颁发诏敕的信物,正面和背面分别刻有汉字和契丹文,这是至今发现的惟一一件成吉思汗文物实品。
史树青:后来我告诉国家文物局张文彬那儿去了,国家文物局局长。我说张局长,你得帮忙啊。张局长说,我说您一定给河北省大成县,河北省文物局局长打电话,这东西放不了,河北省不要咱们要,这是个国宝啊。
主持人:后来河北省要了吗?
史树青:河北省不要,张文彬要过来了。
主持人:等于最后还是拿到国家博物馆来了。
史树青:据说河北省——后来我了解一下——也嫌贵。两万多块,后来送回来之后可不是嘛,两万五买的。
主持人:他又涨价了。他知道您回来又再去要的时候——我们今天也遇到这种情况,一个小牌您没看之前卖三百,您看完之后掉头走了,我们再一问他就卖五千了,这种情况是不是经常发生。
史树青:是,可不是嘛
解说:1919年,史树青出生于河北乐亭县,14岁那年,随父亲到北京上学并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当时的师大附中与京城著名的古玩市场琉璃厂仅一墙之隔,正是在这里,史树青开始了最早的捡漏生涯,也正是在这里,他花两毛钱捡到了这辈子最大的一个漏。
史树青:我14岁进师大附中。我父亲也常去,我放学的时候也常去,我就跟他们很熟了,我听他们讲话,听他们的言论,听他们讲的故事,就记得很多了。
主持人:这个眼力眼学是不是就这样逐渐逐渐练出来了。
史树青:对,当然了。我用两毛钱,差不多相当于两毛钱就买了一个字画,谁的呢,邱逢甲——清朝末年,台湾人。台湾的字画落在琉璃厂棚子里挂着没人买,我两毛钱买了,
主持人:当时没有人知道。
史树青:没人知道,我知道邱逢甲这个人啊。两毛钱!邱逢甲!国宝现在是。我就保存,解放台湾那个展览我捐了。我捐了这个,我高兴。
解说:至今,著名爱国人士邱逢甲的这幅真迹仍然存放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仓库里,这幅当年两毛钱买的画现在是国家一级文物,捡到这幅画的时候史树青只有15岁。之后七十年的岁月中他捡漏的爱好就一直没有断过。1938年,史树青中学毕业,并考上了北平辅仁大学,当时的他已经在书画鉴定界小有名气。
史树青:中学毕业老师就给我作诗,赞扬我懂得书画。“书画常叫老眼花,鉴藏年少独名家。”
主持人:那时候夸您呢。那是当时您鉴定了什么东西,让老师印象很深?
史树青:那是郑板桥。郑板桥一张画,都看不好,我说是真的。结果到琉璃厂他们一卖,真是真的。
主持人:那些老师说是假的。
史树青:老师们都不懂,看不好,都二乎、不确定。
主持人:那您怎么就敢断定它是真的呢?
史树青:我看郑板桥的东西很有经验的,我家里都有郑板桥的。我看郑板桥的书,看郑板桥的字。看年代。
主持人:我觉得说一个东西是假的比较容易,说它是真的不太容易,因为更何况您当时那个老师——不是一个老师,好几个老师——都说它是假的。
史树青:都不敢表态。
主持人:那您为什么就敢说它一定是真的?
史树青:我就是敢说,我相信,自信力很强。
主持人:在您印象当中有没有看错的时候?
史树青:真没有过。大错真没有过。错就是错,正确就是正确,看错了我感觉不多,没有特殊的什么看错的东西。
主持人:有没有您肯定了的东西,但是有别的大家给否定?
史树青:那多了,那有。
解说:在文物鉴定界,其实围绕一件文物各执一词的情况经常发生,甚至很多文物的鉴定最终也不能定论,像史先生这样的大鉴定家经常也会面对一种两难的境地。
史老:真就是真,假就是假,如果是我的水平不够,我看错了,那我的责任,我不对的。我全是根据我自己的水平、根据我的认识,认为它就是真。假就是假,也不说违心的话。
主持人:但是您会不会不说话?经常搞文物鉴定的时候,一个东西有时候他们会不表态,会笑一笑?
史树青:有时候是假的,他不乐意发言,不乐意参加讨论。
主持人:您有这样的情况吗?
史树青:我是如鲠在喉,无论讲话。真是真,假是假,必须发言,我不发言谁发言哪?我是懂得这方面的人。
主持人:也就是您只会对这个文物负责,不会对这个文物的人负责?
史树青:对事不对人哪。
主持人:不考虑是谁来问?
史树青:不说违心话。
主持人:那您担不担心因为这个使得某些人不高兴,甚至成为对您的一些把柄?
史树青:我不担心这个。真就是真,假就是假。我的看法,凭我的水平看的,我绝不说违心话。
解说:从进入国立博物馆的那一天开始,史树青从最早的书画鉴定不断扩展到各类文物,大到陶瓷器皿,小到一枚印章,经他鉴定的文物有上百万件之多。在博物馆工作了这么多年,史树青曾陆续把许多收藏的珍贵字画捐给了博物馆,除了邱逢甲的字之外,最著名的是这幅1956年捐赠的《海瑞行书轴》,因为这幅字,在文革时史树青被批为了三家村的帮凶,挨过各种批斗,一番好意向国家捐赠却引来想不到的种种罪过。文革后,史树青一如既往地有好东西就捐,最近,他还决定将自己从地摊上买的一把古剑捐给博物馆。
史树青:只要博物馆需要,展览需要我就捐。
主持人:那您会不会觉得您捐了以后自己挺遗憾的。
史树青:我高兴,我高兴。你像邱逢甲这个东西,我跟捡了的一样,现在算是一二级文物。
主持人:其实干您这行,我觉得在我们看来,总是跟财富有关系。
史树青:有钱的才能收藏啊。而且生活提高了。
主持人:像您这样有眼学的、眼力非常好的,可能您随便看一看,您自己去买一点东西。那就是好东西。
史树青:我也认为是好东西。到现在我这老伴、我这个女儿认为我买的东西都是假的。认为我买的都是假的,瞎花钱,不让我买。
主持人:但是您如果,只要您买一件……
史树青:我认为都是好东西,我家存起来的都是好东西,就是存的几百张字画也是好东西。
主持人:现在有很多收藏家,他买的东西他会让它进入市场,一旦进入市场也许他当时花很少的钱买的东西就会变得非常有价值。我相信如果这样做的话,您夫人也好,您孩子也好都不会认为您买的是假的,您为什么不这么干呢?
史树青:我没卖呢。
主持人:您为什么一件都没有卖呢?
史树青:我搁着,收藏家搁着。
主持人:您真是收藏它?
史树青:真收藏!
主持人:可能对于您这种搞文博鉴定、喜爱这样的文物的老先生来讲,您看到这样的东西都会感到……
史老:我亲切,爱文物就是爱护国家的文化遗产。爱国主义!外国没有的,中国有这个东西不得了的,都是祖先的遗留。很有意思的。
解说:虽然已经年愈八十退休在家,但每天到史老家中登门拜访、请求鉴宝的人络绎不绝,每每他们都被史老渊博的学识、丰富的学养所折服。鉴定的时候,史先生从不需要借助科学手段,他老人家一打眼,就能辨别出文物的真假伪劣。
史老:科学有误差。
主持人:这误差在什么地方呢?
史树青:科学东西鉴定的科学标本你都没谱,原料鉴定都没谱,取样都没谱。
主持人:比如说像清朝的一些纸今天还有,但是我们用今天的方式去仿造一个画,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呢?
史树青:有啊。用旧纸画画做假画,有这个情况。
主持人:这样您鉴定这个纸的时候肯定这个纸是旧的。但画可不是旧的。
史老:这个事情真是难。我们凭眼力看的人呢,往往不相信科学鉴定。都是凭眼学来看的,目前还是。
主持人:这个眼学是怎么练成的呢?
史树青: 这一点儿,我的读书。我现在还有几万册书。书还是读得不少。
解说:北京东堂子胡同里的一间旧四合院是史树青原来居住的地方,在这里他住了四十多年,这里还藏着他多年积累下来的三万多本书,这些书是史老一生最大的财富,也是他丰富眼学的最根本源泉。
主持人:我听说您到现在每天晚上还读书读到两三点?
史树青:必须读书。
主持人:您这个书是怎么个读法,您原来读书的时候会背它吗?特别是您会看重那些内容吗?
史树青:背目录,可以说是一门书皮的学问。
主持人:就一定要知道有哪些书是关于哪些内容,然后它的名字是什么,是什么时候写的?
史树青:真正除了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以外读的书也不多,就是《诗经》、《楚辞》,读的书还没读全。
主持人:《诗经》、《楚辞》你觉得还没有读权,但是您会记目录、记书皮。书皮学?
史树青:书皮学。我这个书皮学问,你们学一辈子你们也学不了。
主持人:您是觉得书皮学问很重要?
史树青:很重要,很重要,书皮学问太重要了。
主持人:他能够使您在需要的时候知道到哪儿去找?
史树青:对,哪儿找去。书到用时方恨少啊。现在知道这个书名就不容易,知道书名学就不容易。
主持人:您认为这个比读那个书本身还重要?
史树青:当然,这叫竭泽而渔。你给这个东西弄净了,周围打扫净了之后你再研究,超过他们、后来居上,不然的话你还落在前人的窠臼里头不行了。
解说:史树青一生为学、读书无数,披沙拣金、征史探源,终成就一代大家,但遗憾的是,今天史老却感觉满肚子的学问无以后继。
史树青:现在的学生读书太少了。我一个学生,硕士研究生,就是嘉德公司副经理,女的。我还有一个学生苏浩,他下海了,就是中贸胜嘉拍卖公司的经理,他干这个了。
主持人:您对他们的选择您怎么看?
史树青:就是有一个日本朋友叫迟田温,他就跟我说,我是在外语学院,在日本研究所教课,我们教的学生都是希望他们出去之后搞学术研究,没想到外语学院毕业的这些学生,日本研究所的学生出来之后都搞了商业了。他说我非常伤心。
主持人:您呢?
史树青:我也是这样子——不是搞学问了。
主持人:那您希望您的学生怎么样?搞学问?
史树青:读书。学术见解这很重要。
主持人:你觉得商业会耽误他们的学问?
史树青:当然耽误学问了,我们是研究学问。
主持人:您对文博鉴定的事业、您对未来,您怎么看呢?
史树青:还得培养。
主持人:您的眼学可以传给后人吗,传给学生还是传给您的孩子?
史树青:我感觉传给后人很难,孩子很难。这个事儿,我儿子也学我这套,他往后到潘家园到那儿买东西,一买我一看就是假的。他认为他懂,认为比我懂,瞎买。
主持人:还是眼学不一样?
史树青:他不懂这个,没搞过这个,瞎买啊,瞎花钱哪。现在我就苦于没人懂我这学问,这个是一种绝学了可以说是。
主持人:您觉得您这种眼学会会变成一种绝学?
史树青:我感觉是绝学,我感觉我的学问——我不敢跟大专家相比——我感觉我这个学问很深,不是吹呀。很深。
解说:最近,史老以前住的四合院就要拆迁,他最担心的是他三万册的书该如何处置。子女们都不要这些破烂,而史老的爱人夏老师好整洁,也不愿意把这些旧书都搁到新家里。为了这个问题,史先生夫妻俩争吵了很多次,最后史老妥协了,在史老现在的新家,我们看不到多少旧书。而每次重新回到四合院的老宅子,史老都要吵着把一些已经装箱的书拿出来再看一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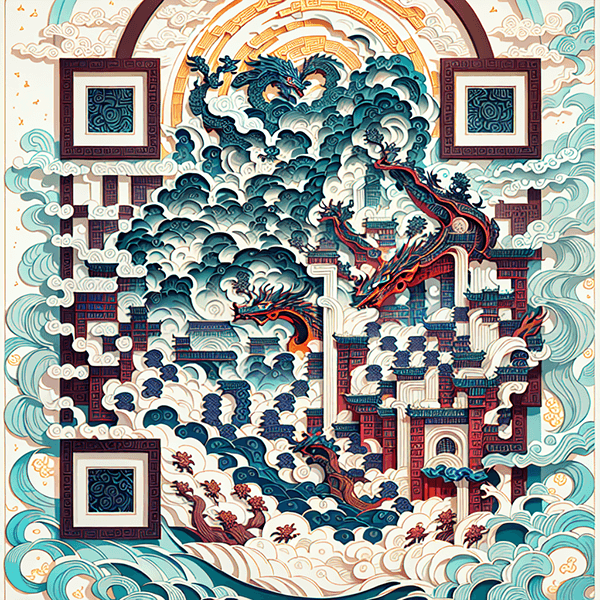
本站文章禁止未经授权转载,违者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授权请联系:etang114@163.com
免费鉴定 重金收购| 艺唐书画韩剑先生【微信etang114】13772099114长期收购刘文西、王西京、崔振宽、何海霞、于右任、方济众、石鲁、赵望云、贾平凹、舒同、晁海、郭全忠 王有政、王子武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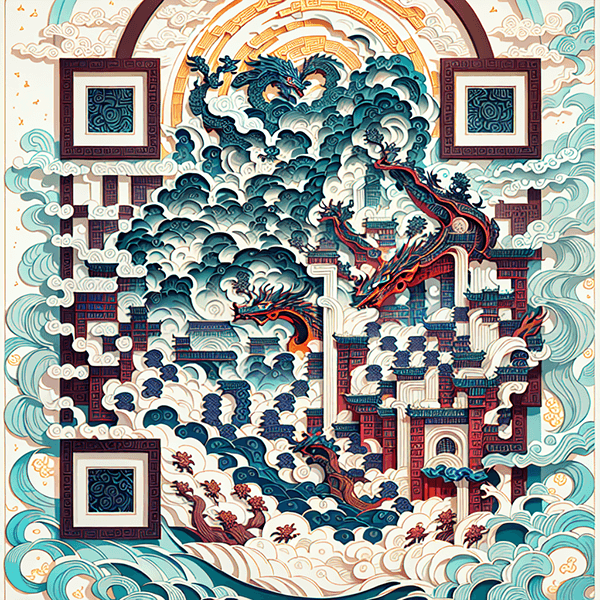
共 1 页 1 条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