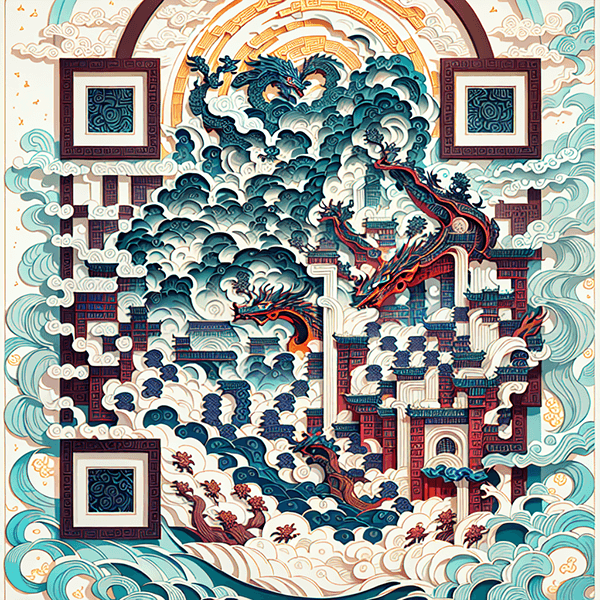书香多姿有健笔
编者按:今年是五四运动105周年,也是陈独秀诞辰145周年。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自然要关注陈独秀。围绕陈独秀,研究者们钩深索隐、刮摩淬励,以拂去历史尘埃,还原事实真相。本期“文史钩沉”特刊发相关文章,以飨读者。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五四运动让独秀精神得以弘扬。2009年的“五四”,我与陈铁健先生应海南朋友之邀赴南国作“重读陈独秀”之讲座,会场设在海南大学礼堂,陈铁健先生讲重估陈独秀著作的历史与学术价值,我讲陈独秀首先是文化领袖,独秀长孙陈长琦讲爷爷陈独秀的故事,《海南周刊》以两版的篇幅报道了我们的海南之行。讲座之余,我第一次得以与陈铁健先生畅谈种种,双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研史当无穷尽
陈铁健(1934—2023)网名铁翁、老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有名的才子,以中国瞿秋白研究第一人的声望,出任中国陈独秀研究会第二届会长。“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政党史,尤其研究中共革命史,自然关注书生革命家、中共建党第一人陈独秀。陈独秀研究会创始于1988年,会员多时达千余人。1997年5月,研究会在上海召开会员代表大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林茂生(1929—2005)请辞研究会会长职务,推荐在下接任。在下忝列会长七年,结识不少学者,其中就有石钟扬君。石钟扬先后著书五六本,同时致力于收集陈独秀手迹。”这是铁翁在《陈独秀手迹序》中勾勒的中国陈独秀研究会简史。学会里铁翁的稳健与学会执行会长唐宝林的激进,相映成趣;京派学者与海派学者既合作也竞争,也成一景;学术立场与学术资源决定以近代史、党史界为主体的京沪学者多善宏大叙事,而游离于京沪之间的皖派学人,我只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小题细作(不敢称小题大做),如对陈独秀之小说理论与创作、诗歌理论与创作等几乎无人问津的小题目力求写清写透。与会长、执行会长偶尔在陈研会上相逢,也仅点头之交。
直到2005年2月,拙著《文人陈独秀》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意外地引起学界尤其是陈研界的重视。我对陈独秀的定位为:他首先是文化领袖,其次才是政治领袖。作为政治领袖,他是个悲剧人物;作为文化领袖,他呼唤的科学、民主具有永恒的魅力。
2005年6月15日,铁翁有信致我:
钟扬兄如晤:
昨自兰州大学客座返京。在兰州一月有余,除与学生接触,外界已无联系。今日到所,得兄所赠大作,印象之佳,实出意料。从别一角度审视独秀先生,史有真实,文有丽彩,哲有思辨,确为佳作也。
今夜車赴苏州,后日到常州开瞿秋白学术会议,廿一日到沪讲课,约六月廿六日返京。将有小书寄呈指教。耑此即候。
陈铁健手奉
二〇〇五年六月十五日
2009年10月,拙著《文人陈独秀》再版,铁翁、李锐、冯其庸、叶尚志四老皆有诗相贺,出版社将他们的手迹影印做了前插。铁翁诗为:
往事迷离未足奇,不疑之处应有疑;
似明若暗理还乱,研史当无穷尽时。
此余治史一得之见,愿与石钟扬君共勉并贺大作重刊。
己丑春正,陈铁健(印)
2010年7月,拙著《五四三人行》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前有铁翁之序,充分肯定此书“论据妥帖,晓畅明白”,“史学家不易写出这样的文字,而从文学走近史学的钟扬,似乎驾轻就熟,游刃有余”。文末更语重心长:
科学、民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真精神,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五四三人行,就是五四精神的杰出创造者和体现者。对他们的评价、接受与反接受,正好检验着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和历史走向。
前路多曲折,回头路却断不可走,那是一条不归之路。
铁翁《书香人多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4月版)、《寻真无悔——陈铁健八十文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版)皆收此序,尤其是《治史唯真》(当代学人论学墨痕丛书陈铁健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8月版)收有他对《五四三人行》的手书笔记,则见其对拙著的错爱。
弘扬独秀精神
我策划的纪念陈独秀130周年诞辰书画展,仗陈独秀人格魅力之感召,获得书画界、学术界,尤其是陈研界朋友的支持。然以种种缘故,2009年展事未果,移到次年的10月9日在江苏省老干部活动中心开幕,故称“迟到的纪念”。铁翁不仅提供作品、邀京城名人参展、出席开幕式,还为我与虞友谦主编的《纪念陈独秀书画选》(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12月版)撰有序言,热情礼赞这以“弘扬独秀精神——科学民主”为主旨的书画展,在历数李锐、冯其庸、叶尚志诸老诗章之余,他说,他也技痒,献上俚句两则:
其一
学开新宇,神存万古;本色书生,大哉独秀。
其二
千载流芳陈仲甫,秋实春华新青年;
独引德赛驱蒙昧,秀满乾坤足称贤。
2012年5月26日,在南京财经大学图书馆召开“陈独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学术研讨会”,铁翁、唐宝林、沈寂、李银德、沈建中等全国几十名学者到会,铁翁在开幕式上作了主题报告,其面带微笑,轻言细语,徐徐道来,以严密的逻辑推出鲜明的观点:中国现代化进程任重道远,以陈独秀为精神领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化之光辉起点,颇具感染力,为大会奠定了基调。
荐友砥砺学术
铁翁以他的人脉为我引荐了不少朋友,其中三位印象尤深。
其一为铁翁的吉林大学历史系同学、黑龙江大学哲学教授郭立田(1935—2023)。他受铁翁影响而爱读我陈研著作。2014年5月,郭立田撰万字长文《评石钟扬新书〈一个时代的路标〉》(《海周刊》,2014年6月16日),赠我康德《判断力批判》文本解读与《人本主义美学概论》及未刊本自传《一个人的追求》(署名“海之潮”)。自传分学生时代、苦难岁月、翻身日子、新的奋斗四个部分,计有50万字,写了他求学、劳改、平正、新生过程中的学术追求。郭立田将未刊本自传寄我,让我润色或改写。感谢先生超常的信任。我询之铁翁,铁翁说自传怎么改写?于是,我置之书架不敢妄动。
2023年1月5日,郭老师病逝。1月9日,铁翁于微信朋友圈发文悼之,堪称郭氏小传,慨叹命运与才情之余,深赞其“劳改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劫后余生,由史转哲”,“其志益坚,思更深邃”,笔耕不辍,“退休前后,著述之余,连年培训人才,生财有道,广置海南三亚、五指山房产。盛情邀余及诸学友移居琼崖,十余年间,屡聚山间湖畔,谈天说地,纵论古今”。反思郭立田遭“五七”引蛇出洞“之劫”,铁翁说:“时余为年级党支书,奉命批右,与有罪过焉。”在这忏悔意识稀薄的土地上,铁翁之言尤为可贵。有一次,郭立田邀我与铁翁夫妇到他难友豪宅小聚,叙旧时常老师快人快语:“郭老师右派就是老铁打的。”没等铁翁开口,郭老师抢着说:“我是在劫难逃,他不打,别人也会打。”君子坦荡荡,此恰是他们至死不渝友情之基石。
琼崖六贤至此其中三友先后远行,铁翁深情地说:“虽死犹生,情谊不减反增,人间天上遥相望,终将相逢有年时,永驻天堂,再无分离。立田千古。”
其二为“天下最好的主编”褚钰泉(1944—2016)。2013年秋,经铁翁推荐,我才读到褚钰泉主编之《悦读MOOK》(以下简称《悦读》),并开始为之撰稿,有相见恨晚之感。我给的第一篇稿子是《陈独秀脱帽记》,是一篇旧稿改写的。《五四三人行》原稿有上篇《五四现场:思想启蒙的境界》,下篇《五四后劲:再造文明的努力》,外篇《五四情结:民主进程的史鉴》。全书写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与“五四”的故事,外篇乃推论他们在1949年后的命运,寻求“五四”传统存亡的历史原因。未经送审,出版社就自觉砍了外篇,使之成为断尾巴的蜻蜓。阅读几卷从铁翁那里获得的《悦读》,冥冥之中觉得可与之结缘。于是,我将那蜻蜓的断尾巴寄给了褚钰泉,实则将这个难题推给了他。不久接到褚钰泉电话,建议从几万字的外篇单抽出陈独秀话题整理一下给他。文章先讲毛泽东的独秀观,然后说几十年来民间与官方良性互动,艰难地还独秀一个本来面貌。拙稿在《悦读》与《文汇读书周报》同时刊发,引起一些朋友与媒体的关注。
从此,我与铁翁一样也成了《悦读》较活跃的作者。从2013年底到2016年元月,两年多时间,褚钰泉连续以“特稿”推出我4篇长文。2016年1月8日这天,褚钰泉有信有电话,还有短信向我问候并询问近日在写什么。诚如铁翁所言,主编非常尊重作者,他之约稿与改稿总是以商量的口吻与作者沟通。当时我手上正有一篇《毛泽东与中国小说》,准备春节后给他。不料,次日——那黑色的清晨,褚君竟以心脏病发作而猝逝!我与之素昧平生,成了他的作者也未曾谋面,从此却阴阳两隔。
铁翁在微信朋友圈痛悼褚君:“天下最好的主编走了!《悦读》不再,已成绝响。”引发同道广泛的共鸣。
其三为北京三味书屋老板刘元生。三味书屋在东长安街头,专营高档人文书籍,域内似乎罕见(天津之天泽书店堪称同类),也是域内人文学者与读者之打卡地。书店上下两层,各100多平方米,楼下为书店,楼上为住宅与演讲厅,诸多学者曾在此作过精彩演讲,铁翁即在其中,以“弘扬独秀精神”为主要话题。
2018年10月中旬,我在河南开封金学会议之后赴京与某出版社谈“五四”百年之书稿,铁翁携我两访三味书屋。
江津是陈独秀生命的终点站。一批年轻的朋友非常敬业,把陈独秀旧居陈列馆(简称“秀馆”)打造成了重庆的文化地标之一。秀馆多年来每逢“五四”,都请铁翁与我去作讲座。讲座之余,由邓野或别的朋友陪我们在重庆若干文化打卡地转悠。每次还有个保留节目,就是到江边或河滩捡石头。2019年4月25日,我与铁翁在秀馆参加“五四百年图片展”开幕式并作专题报告。26日下午,邓野与我们一起去了宜宾李庄。抗战时期,李庄只3000居民却接纳了读书种子1万多人,成为战时中国一座最具影响的学术城,我们怀着敬畏之心寻觅着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的芳踪。在李庄江畔,铁翁竟发现一枚有甲骨文图案的长江石,可谓独具慧眼。
铁翁有情有趣,“看书、写作我都很玩命,要玩我也很玩命”。有次答记者问,其如是说,最见性情。收藏仅是其多种雅玩中的一种。2014年,他意外受伤,到潘家园淘得一旧手杖,杖首刻字显示竟是北大“怪杰”辜鸿铭之遗珍,令北大校史馆的朋友惊羡不已。其所藏书画金石尤其是砚台,皆以独特的审美眼光所获。
以审美眼光视之,铁翁觉得陈独秀手迹弥足珍贵。他在《陈独秀手迹》序中说:
独秀先生手迹,尽显其人喜、怒、哀、乐、狂、直、耿介、率真的人格魅力。其书各体皆备,不攀门户,崎岖雄健,风骨充溢,而毫无甜媚、浮滑、做作与匠气。
先生手迹是他深厚学养与书生本色聚合的书艺珍品,是他早年启蒙、中途歧路、晚岁彻悟的人生展示,是他“永远的新青年”“终身的反对派”的真切记录,更是中国近代艺术史重要节点上不可忽视的宝贵文献。
铁翁曾两次带我到近代史所档案馆拜读陈独秀书札真迹,并就如何使用这批手迹为我进行过有效的协调。铁翁最上心的是拙编《陈独秀手迹》,最操心最不放心的也是这部《陈独秀手迹》。《陈独秀手迹》与陈独秀一样命运坎坷,这些年来转辗多个出版社,出版合同屡签屡毁。诚如铁翁所云:“手迹出版成本昂贵,又不无风险。出版家口赞者众,实助者渺;即使热心响应者,也因经费不足,报批困难,往往始诺而终弃。”2021年6月,好不容易与荣宝斋出版社签下出版合同,他们也动手编辑出样稿。铁翁似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他兴奋地为之手书序言,欣喜地称:“石钟扬挫而不馁,周密运作,终得北京荣宝斋出版社慧眼识珠,拍板接纳,做成至精至美之作,且分文不取。足证今日域中仁者智者仍不乏人。此真学界之幸,国人之幸。”
本站文章禁止未经授权转载,违者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授权请联系:etang114@163.com
免费鉴定 重金收购| 艺唐书画韩剑先生【微信etang114】13772099114长期收购刘文西、王西京、崔振宽、何海霞、于右任、方济众、石鲁、赵望云、贾平凹、舒同、晁海、郭全忠 王有政、王子武的作品